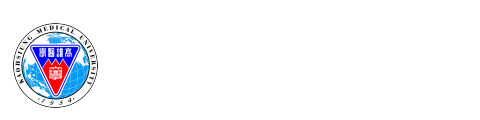松鼠會擱淺嗎
那隻松鼠頂著突兀的肉色鼻子在水泥馬路上亂竄,又紅又亮的鼻子讓我想起魯道夫,在漆黑的夜拖著沉重的雪橇劃破天際的領頭馴鹿。牠稍停一會便略帶遲疑地向一人一狗湊了過來。「牠受傷了嗎?」隨著一聲驚呼,又倉皇逃離,如飛也似的箭,隱身於雜草叢中。我只當這是一場奇遇。
約略一週過去,當我差不多忘了魯道夫時,卻再以預料之外的方式重逢。
沿著尋常的散步路線,小黃總是跳入一旁地勢稍低的荒地中仔細嗅聞,等待早已是見怪不怪的主人的義務。也許是被腐臭味吸引吧?牠像是發現了甚麼新奇的玩具似地,托跩著我強行踏入垃圾與雜草漫步的禁地中。黑乎乎的一塊,遠看倒像坨司空見慣的流浪狗的排泄物,我不耐地將牠跩了回來,慣性使我的身體自然前傾,我不住定睛一看,那坨排泄物遍布著細毛,再仔細一看,排泄物還有頭、有身、有尾巴,側身俯臥著,僵直的腹背異常地拱起,殘破的臉已無完整形狀,類似眼珠的部位空洞晦暗,吻部早已無法辨識,也不見那突兀的肉色鼻子。我無法判斷他是不是魯道夫,也無從得知牠死了多久、怎麼死去,只知道牠早已死了,成為一隻死去的松鼠。
那一晚我躺在床上想了好久,想著牠的遺容,想著牠的死亡,想著為何魯道夫讓我有種莫名近乎的熟悉感,彷彿曾預見過這副模樣,又彷彿經歷過這副場景。在半夢半醒之際,我突然想起了Z。
Z在我的記憶中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少年,非主流的那種,又或許,唯有在我的定義中,他才會被歸類於美。Z的頭身比相當怪異,倒三角形的頭顱頂在削弱纖長的脖子上,有著高聳的山根和渾圓杏眼,五官聚在瘦小的臉頰,像是東拼西湊的拼圖,彷彿那些口眼鼻並非原生於此。那時的他身高與我相仿,卻出奇地瘦削,修長的四肢清楚可見浮出的脈絡與筋節,Z的皮膚非常的白,不是白裡透紅的白,彷彿半透著光的瓷器,精緻地叫人唯恐一碰就碎,若再湊近點觀察還能發現他頷頸上青筋的跳動,從遠處看那輪廓彷彿再現了瘦長人的獵奇傳說,於是Z有個近乎戲謔的稱號,班上的孩子都管他叫外星人。
然而Z並不是個如外表般病態脆弱的少年。Z是短跑賽的強棒,囊括各個體育競賽的獎項;在課業上,也只略遜色於前三大巨頭。Z的脾氣很好,他任由班上的孩子「外星人、外星人」的叫喊,總是笑著回應這群幼稚的同齡人,但並非無奈地苦笑,他的笑容透露著堅毅,流露著不卑不亢的骨氣。Z是個不折不扣的冷面笑匠,總是冷不防脫口而出幽默的言語。
Z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卻都不在於此。Z總是堅定地看著對方的雙眼說話,斗大的雙眼炯炯有神,他離去的步伐在夕照下顯得堅毅自信,背影隱約流露出不同於這個年紀的早熟。午後放晴的日子裡,他還會帶著一把長傘,若是自他身後呼喚他的名字向他道別,Z會頭也不回地一面邁開步伐向前走,一面揮著他的長傘示意。他的背影在我眼中,形象是如此飽滿,猶如破釜沉舟的壯士,堅定不移地前行。
直到某一日,老師把幾個同學叫去(當然也包括我在內),問了幾個關於Z的問題,問Z最近的人際關係,問他的課業學習如何如何,問他最近和我們聊了些甚麼,問我們有沒有看見他身上的傷,問了一連串莫名其妙的問題,像個偵辦著重大社會案件的刑警,卻不願透露半點內幕。
後來才多少打聽到,Z最近開始會自殘。據老師所言,那個穩重早熟的Z,開始隨手摔東西,拿美工刀割自己的手,甚至用力地撞向牆壁。Z的父母呢?沒有注意到孩子的狀況嗎?Z的父母早已不知去向,只有被Z脫線的狀況嚇得驚慌失措的阿嬤。Z有接受輔導嗎?他說他覺得很吵,一直有人在他的耳邊尖叫,自己也開始說起沒人聽得懂的語言。Z有轉介到精神科診所嗎?Z定期到溫柔女醫師的診間追蹤,但阿嬤說他一顆藥也沒吃,全丟進了垃圾桶。Z生了甚麼病?老師說他是文組的,他也不知道,只要我們多關心關心同學,為甚麼都沒有發現朋友的異常。
當然我們也很想幫助Z,然而Z彷彿早已洞悉我們的意圖一般,開始逃得遠遠地,他的眼神不再堅定,像是恐懼著些甚麼不安地游移,空洞的深淵中彷彿把所有的光亮都吸了進去。Z的步伐不再自信,他的背影顯得佝僂而蹣跚,嘴中時不時振振有詞叨念著甚麼,託散在風中。那群猖狂的青少年仍一如既往地叫喊著:「外星人、外星人,說著外星語」,Z不再笑了,如困獸般惡狠狠地瞪著,杏眼圓睜的模樣讓人感到不寒而慄。
老師不知道的那個病名,我已經找到了,可是再沒有人見到Z了,Z畢業後和所有的朋友斷了聯繫。Z過得好嗎?在很偶爾的時候(或許是看見思覺失調症一詞的時候),會觸發到我心中的那份愧疚,又或許是同情,又或許是惋惜,那份無法形容的情感和記憶,如被鑿開而湧出的泉水般潰堤。思覺失調的正名也好,詮釋此症的熱門影視作品也罷,一切對於我而言似乎又沒那麼重要了。有時我會唾棄自己的無知,有時卻又能對自己釋懷,因為即便知道了病名,我又能為Z做些甚麼呢?況且已經再見不到Z了,也許Z真的是個外星人,他的父母早已接他回自己的母星,有時我甚至會冒出這樣的想法,連自己都覺得荒謬可笑。
那天晚上,我反覆地想,想著Z,想著魯道夫。我做了許多的假設:若是魯道夫並沒有逃離,會如何呢?若是小黃抓到了魯道夫,情況又如何呢?若是魯道夫去了獸醫院,牠會康復嗎?再多的假設又如何呢?就像黑箱裡的貓,連薛丁格都未能決定他的存亡,無人能決定魯道夫是否能獲救,也沒有人能決定刻在Z血液中的原罪。唯一能夠確定的是,下次散步時,我會著小黃,帶著母親佛桌上用清水和白瓷供奉著的那朵鮮花,謹以此獻給不再逃離的魯道夫,獻給與魯道夫極為相似的Z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