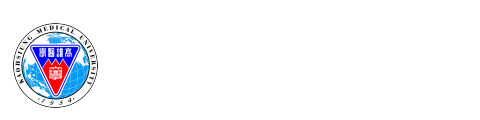我們的房間
一樓客廳後面是阿公阿嬤的房間,阿公過世後,國小的堂弟開始睡在竹編的雙人床墊,阿嬤躺在一旁鋪著厚被子的長木桌,她總是睡在令人費解的地方。十個人住一棟房子,叔叔嬸嬸的疆域分配在三樓,兩個表妹睡在廁所旁的小房間,用白色簾子劃出分界。
我們的房間在二樓,這裡的領土有最多房間,不過我們都睡在太陽升起那側的六坪裡。
禮拜五調課,臨時決定回家一趟。於是叫車下東港,買票回琉球。冬末的遊人少了很多,除了鄉民便是嚴重海洋成癮患者,不下水就挨不了冬。比起十幾年前的五艘船,這些年四艘退休,倒是多了近十艘新的。原先四十分鐘的航程,如今一刻鐘就差不多到了。
小時候對船充滿恐懼,卻又對本島一切抱有期待,看著對岸夜晚燈火,比天上的清晰明亮。我非常討厭船倉的氣味,那股味道從內部溢散至排隊入口,即便不暈船也是噁心作嘔。搭船前母親會買一條葡萄味飛壘口香糖,讓我貼在鼻子前,聞那股甜膩的香精味,安穩度過潮起潮落。
離島就讀的日子七年了,習慣這座島容易蛻變,卻依舊愛那些不變的。我不再暈船了,船的氣味隨著年紀稀薄,只是海還是在,我被推著向前,也被沖著上岸。
打開我們的房間,全是母親的香水味,她習慣每次出門前往裡面按幾次噴頭。木板門的淺黃表皮已經翹起,露出底下粗糙的質地。開門右測是母親的衣櫃,依靠我與弟弟各一的塑膠置衣櫃,爸爸的衣服放在隔壁間的儲藏室。衣櫃上面擺放母親結婚時拍的沙龍照,光滑的深棕大波浪流淌孔雀藍禮服,在銅製的雕花相框裡,如宮廷的肖像畫。
門左側除了電視機外,幾乎整面白牆都掛上大小形狀不一的相框。爸媽裹著麵粉樣的妝,白紗摟在西裝後頭,露出一樣的眉彎和一樣的笑容。旁邊的方框站著我,融於溜滑梯的黃昏裡,接著是我跟弟弟的照片,看起來滿溢稚氣的合照,我們站在一塊石頭前,搭著肩手指向遠方。諸如此類的生活照大概有二十張,卻大多忘了當時的光景。
剩下的相框是國小、幼稚園的模範兒童獎狀,母親覺得它們有其依時序掛列的必要,就算黏膠掛勾時常脫落,隔天也立即想辦法重新掛上,捨不得那面牆留一片空白,也甘願看上面斑駁的殘膠。
電視機對面是雙人床,巔峰時期可以在上面躺四個人。這使我想起國小那時,家裡的50c.c.摩托車也曾擔起如此重負,在每個飯後的環島時光裡像墨魚吐著煙,遊蕩在海浪般的陸地,直到我升上國中才光榮退役。
床的的秩序是這樣的,我們橫躺在長方形的長邊上,才能有效運用有限的空間。我在靠牆的內側,往電視那頭依序是弟弟、母親、父親。一張床,三條棉被,五顆枕頭,如何分配是道難解的數學題。我們卻在那張彈簧與泡棉上度過十六個四季,數不盡的颱風天與熟睡中的地震。
放下行李後,我累得撲到床上,床單花色是深海的寧靜,搭配幾何圖形。雖然床墊也經歷幾次改朝換代,身體陷入的深度與肌膚觸覺依然是熟悉的記憶。如今只剩母親獨自佔領這片汪洋,而父親則另創一畝疆域,於是整個房間被中央兩張床墊分界,一上一下割據床架與地板。
躺在屬於我的位置,已經變成母親一人的形狀了。時間在床上沉積,形塑最舒適的睡姿,牢牢地記載身體的通史。
頭頂向著窗,窗簾舞動,搖曳的皺褶捲起層層波浪。陽光從窗外輕敲,走入鵝黃的纖維與古典花樣,化作跳動的波紋,隨風漂蕩木質衣櫃上。
我們的房間聽得到鄰近的海,喃喃低語。
包覆在柔軟中,想起無數金黃的早晨、黯淡的晚冬,而夜長夢多。
幼稚園做的夢沒有周公,倒是媽祖、玉皇大帝、觀音娘娘等大咖常來作客。遇到這些神明可不是平靜安祥的夜晚,因為爸媽同時站在兩旁,告訴我要去當神仙了。我怎麼辦?於是請求這些神明們不要帶走父母親,又拜又跪,把泰山喊得山崩,把瑤池哭起水難。直到被溫熱的淚水洗把臉後驚醒人間,手馬上伸向母親,確認父親的打呼聲還在,才了卻心事,感恩神明天地良心。
隨著弟弟出生與身體成長,床變得更加消瘦。睡眠成了障礙賽,入睡關卡是父親的鼾聲,高哮低鳴與睡姿搭配招式,隨呼吸消長而頻率錯落有致,須將其聽為紡織娘跟暗光鳥的同夥,當成天籟的一部份便足以克服煩躁。夏日會增新溫度感控關卡,因為母親怕冷,常會在室溫達標時關掉冷氣,回溫的雙腳開始探出棉被,找尋風扇的方向,是需要默念心靜自然涼的成佛之路,不過父親往往耐不住禪意炎熱再把電源開啟。
最難以預防的突襲,是弟弟無處不入的手腳,在睡意正濃的時候來一技一百二十度踢腿,組合技翻身右鉤拳,再麻煩一點的上下半身翻轉也略有經驗了。
每一天就這樣過了,被雞聲喚醒,再把八點檔的片尾音樂當搖籃曲,沒有想過青春痘會一顆顆萌出,腳趾一吋吋超過床的邊際。不過我始終記得身旁那面牆的脈絡,龜裂的裂縫蜿蜒曲折,分岔出枝條,像一棵開不了花的樹,有時候換個角度也像一個長髮的少年,站在石頭上望著遠方。儘管重新粉刷,仔細看依然有蓋不住的脈動,和緩的起伏在新的白色之下。
難以抵擋的賀爾蒙在血液流竄,興奮大腦中樞,生活佈滿一片冒名青春的狼藉。爸媽越常「溝通」了,選在自認無人知曉的深夜。
被吵醒的時候,我以為又做夢了。只是沒有秒針提醒,沒有風扇喧囂。
「為什麼不為我講話,今年第幾年了猶是叫我下去拜拜,之前不是講好輪流?」
「拜拜有啥物好窮分欸?」
「不是我愛計較,這是恁王家的代誌,本來就是要做伙分擔不是嗎?」
「對,恁兜彼爿要我鬥相共,我攏無講幾句話。」
「這是兩件代誌......」
「我猶未講你常常去揣榮阿開講......」
「遮講過幾遍啊,榮阿是阮爸認的契囝,你是當作我佮伊討契兄嗎!」
……
「可以不要吵了嗎!我明天還要上課!」
時鐘的聲音回來了,還有風聲。還有一點點,如果用力聽的話,海浪的聲音,稀哩嘩啦稀哩嘩啦在心裡打個不停,有時竟像外公的機車聲,從碼頭到這個村莊。他會帶我去撿貝殼,那裡的海比較寧靜。
通常我不會出聲,背對弟弟,刮著脫落的油漆一片片碎裂。時而仰望上頭的四方型拼貼,無法完美湊滿歪斜的天花板,為了貼合邊框,邊緣的圖形於是被割成了其他不規則形狀。
「為什麼不讓我到隔壁睡!不是還有房間嗎?」
「你沒多少時間可以跟媽媽睡了,這是你孝順的機會欸。」
「那你就不要半夜看電視吵我,煩死了睡都睡不好......」
熱帶低氣壓在小小的房間成形,吸足日常的水氣,飽滿成颱,搜刮每個角落。情緒的渦旋升級或消散,途徑難以預測。有時發展藤原效應,共伴東北季風,劇烈的外圍環流將房間浸泡成海,只為了留下一家子愛的證據。
路燈把窗簾的陰影照在臉上,失眠的夜晚,我勤奮地記著房間的一切。包括鬧脾氣摔門而炸開的木板,婚紗相框不慎掉落地板的凹痕。連插座的縫隙也有段故事,一群螞蟻曾短暫借住半個夏季,我的身體連帶被拜訪幾晚,最後不得不封填驅逐。我還記得清晨睜開雙眼,光芒把簾子的粉塵飄得紛飛,像彼得潘的金粉。好幾年後我也將飛過海洋,三十分鐘8.9浬便抵達本島,途中睡一覺,也不知歷經多少波折,即是新大陸。
回到我們的房間,已經是離家七年,一樣大的房間隨著我們成長,消化內部的事物,回收可利用的記憶,剩下的就忘去。
斷層的白牆會重新粉刷嗎?褪色的照片還會放多久?
離家五分鐘車程,是新家的所在地,到時候我們都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吧。
「欸媽,新家你會跟爸爸睡同一間嗎?」
「猴死囝仔,我不跟你爸睡是要跟誰睡!」
自稱夫妻感情現在很好的母親之後又說,父親叫她去房子內照不到陽光的房間睡,這樣晚起就不怕光芒刺眼;而他自己要睡在靠海那頭,如此早上去釣魚便能先看到日出。
即使往後可能不常回家,我仍希望在漆成蔚藍的新房間掛上滿滿的相框,於是我們像海浪上的漂流物,就算彼此漂泊各方,也在同一片海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