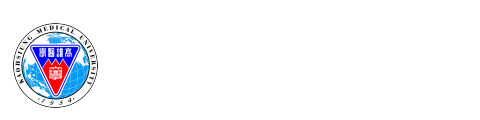貯物癖
黑色塑膠籃倒蓋在地板,依序把紙箱疊起,便可以剛好搆到腰際。來來回回數趟,搬家工人自有其條理,什麼樣大小的紙箱必須疊在什麼樣大小之上,也深諳如何使力才不會傷及腰部的身體技藝。空氣窒著西曬樓厝習以為常的黏膩,透著黑色塑膠籃的一格格孔洞,瞥見地板上繁忙的腳印,自門口一路蔓延至房間最深處,一如這幾年來囤積在此的家當。
那陣子的雨季,挨著陣陣對流雨的間隙,和姊姊在未落雨的空檔之中搬家。後來一、兩日,稍稍放晴時,騎著機車在新家附近晃了幾圈。那是這城市近來炙手可熱的新興建案區之一,蹲踞在縣市合併前的交界地帶邊緣。而就在新搬進的大樓後面,跨過一條淺淺的河堤,卻是一排排形成鮮明對比的舊工廠。隔著那條淺淺的河堤,一位外籍移工假日時好整以暇地坐在工廠的鐵皮屋頂上,抽著厚重焦油味的尼古丁,度過那週他僅有的休假午後。這裡的人們也許已經習慣了,集體背向河堤另一邊的傳產工廠、稻田、野狗、焚化廠,高談闊論比劃著未來這一帶發展的商機與生活機能,像某種儀式般,面向日落的方向做夢。
像一層一層日漸密實的繭蛹,這種新興建案都是一棟棟向外推進的。建商深諳此道,如此一來,每個新買的客戶,都會以為自己是萬中選一、集滿所有幸運點數才買到的景觀第一排,直至某天清晨,被窗外的下一樁地基敲醒清夢。
別人清夢裡的家也許充滿著溫馨的色調,而誤打誤撞不小心租屋此地的自己,對於未來的家會是什麼模樣卻還沒有什麼頭緒。但卻仍記得過去的夢,那總是跳動、總是流動著的家。
*
剛搬來的第一天,客廳才剛整理好,滿頭大汗想沖個澡,一踏進乾濕分離的衛浴我才一愣。彷彿踏入另一個不熟悉的次元,對於從小到大家裡浴室都是有著貼滿彩色馬賽克磚浴缸的我,對乾溼分離浴室的運作,每一個元素、每一件組件置放的方式,都萬分陌生。像不諳算術的人,試圖推敲數學式裡各個符號的用意,或不諳機械的人,誤闖充斥著大型機具的工廠。
正困惑著該把新買的毛茸茸地墊放在濕的那一區外面,還是放在乾的那區外面?又該把浴室用拖鞋放在濕的那邊,還是乾的那邊?好不容易,我們才試著悟出一些道理,把東西依次擺齊。水頭龍擠出一滴鑲著陌生臉容的水珠,黏在潔白的洗手槽上,突兀地試著在新的次元裡,把自己的身體嵌進。
沖完澡,走進房間,雙人床佇立在牆邊,擺完兩三隻孤寂的娃娃,也仍兀自空蕩──這若是在老家,大概是如今仍然擠著媽媽、姐姐和我三人的寬度。
再環顧一眼剛整理好的客廳,在一般的新屋DM裡本該放著電視的地方,擺上從大學以來偷偷買的藏書,四、五個紙箱的量,溢出書櫃的邊緣。那些書,是媽媽會嫌浪費錢、浪費空間、沒有用處的書,彷彿在跟媽媽無聲作對著,它們從客廳書牆,一路蔓延至房間書櫃。
「你們兩個人的東西算多的喔…」搬家工人微微尷尬地說,大概心想價錢開太低了。而我,也只能回以更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,看著吸乾他們藍色小發財車所有空間的層層紙箱、黑色垃圾袋。倘若搬家公司從客戶的東西多寡可以對這人的個性窺知一二,極簡主義者、中規中矩者、斷捨離者……,那我已經可以想像他們在紀錄簿上的註記欄,對我寫下的診斷:「貯物癖」。
成癮似的,貯存所有的有用、無用之物。
*
這樣的貯物癖,說不清從何年何月,小心翼翼地開始在老家鐵皮屋的不起眼抽屜或角落,豢養這個習慣。而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的?也許是七歲家裡因債務跑路的那夜,一個黑色大垃圾袋,七零八落裝載進四個小孩所有的衣服、鞋子開始,那些心愛的文具、收藏已久的貼紙,遺落在出生的那個水泥色平房時候開始的吧。
七歲之前的珍藏彷彿酒吧裡被帶走的斷片,在記憶裡頭空曠無比。彷彿為了補償些什麼,後來輾轉搬過一、兩次家,即便空間在怎麼狹仄與拮据,總會在衣櫃底下的匣子、書桌抽屜與牆壁間的夾層、一個又一個層層疊架起的紙箱之中,留下貯物癖的蛛絲馬跡。空間是無限繁殖的,在這些無用之物間得以無限被壓縮。
曾被媽媽叨念猶如「撿破爛的」──畢竟已長到成年,連國小的畢業紀念冊、畢業典禮上的胸花別針都仍靜靜躺在角落的紙箱裡,彷彿深怕有一天,會連自己十二歲的樣子都不記得。還有高中時第一支手機的充電座,好似擔心哪一天,通訊錄裡、久未連絡的那個誰,會突然再打給自己一樣。每一年的行事曆,則像害怕日子又再度斷片,深怕哪一天遺忘時,找到這幾本行事曆便可以回頭追索記憶的線頭。
貯物癖從何時開始的?又或許是一次次搬遷下,好不容易以為要落腳下的鐵皮厝,卻又在五年前離家之時,媽媽那幾近漠然的話開始的吧。要的東西就帶走,不要留任何東西在家裡,反正一年不過也才回家幾次。她繼續說著,這個家,未來若有了什麼萬一,可能就會賣給阿姨,也不一定一直都會在。
家,從來不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永存。不像建案廣告上常說的永恆的避風港,一次又一次的搬遷讓家的記憶不斷跳動。沒有家,只有物。我只能像蝸牛般,把家揹在一次次搬家時的身上。
要帶走的就帶走,我像再一次大遷徙般,慌慌張張把十八歲前的回憶裝箱,帶往這新城市。在新的城市,學校後巷的街角,吃定學生偏好租金便宜又離學校近的租屋處,永遠只有黑夜似的白晝,永遠沒有陽台。沒有貓狗寵物,只有擁擠的人類,在擁擠的樂園裡頭豢養自己。百葉窗圈住這短暫的、不宜人居的畸形的家,用咖啡因想像白天時光的形狀,用音量適宜的音樂掩埋隔壁的氣息。猶如長了犄角的蝸牛,揹著所有家當,住進殘缺的模子,在新的城市,暗灰色的五樓套房,小心翼翼繼續我的貯物癖。幾年後,終於在新的城市搬到另一個新的熱門建案區,然而貯物癖症狀依舊,不一樣的是,這次貯的,終究變成媽媽看不懂的村上春樹、漢娜鄂蘭、Bob Dylan。
*
坐在書桌前看著書,大片半落地的窗篩著自然光灑下。像與過去一次次搬遷的那些家作對一樣,我只能在新家繼續貯著物,貯著媽媽看不懂的文字、貯著飼料比便當還貴的寵物所掉落的毛髮,貯著生活的肌理,貯著過去那些曾經住過的「家們」的回憶。
搬家工人汗流浹背地離開了,也許還在扼腕開價太低,也許感嘆這貯物癖患者的無藥可救,而外頭豔陽下的工地再次敲下新的另一棟建案的地基,劃破安靜的午後,繼續建造別人夢中亙古不變的避風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