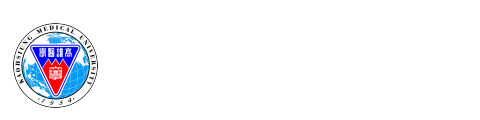我是一個相當依賴預兆的人。
無論是憑藉星座運勢、塔羅牌這類玄妙的方法看透未來一片混沌,或是純以一己之洞察發覺事件的先機都好。我希冀生命得以順著冥冥之中的牽引運行,使邁向明天的自己不至於不著寸縷。
然而,長大以後我才發現,許多事情的降臨都是沒有跡象的。
*
怔忡地掛斷電話、從重考班趕到醫院的公車上,我一滴眼淚都不敢掉,直到看到哥哥才勉強回過神。
腦動脈瘤破裂溢出的血漲滿顱腔,他的雙眼輕輕地闔起,隻手無力地將被單抓緊,胸口隨著有些急促的鼻息微微顫動,彷彿落水時的掙扎。第一次看見各種粗細的、白矇矇的塑膠管線從他身上僅有的小縫隙中穿透而出,才知道那是人在盡頭時的加冕。
二十年的生命忽然就要結束了,毫無預兆的。
被叫進手術室時,我吞回想吐的衝動,抱著母親讓她別過頭,不至於親眼看見兒子腦袋被剖開的畫面。無菌室內的白光像是深怕人看不清似的、大力映襯檯面上的豔麗鮮紅,冷空氣掐著脖頸,地上散落用過的自費止血帶,浸滿鐵鏽色乾涸的血漬。為了避免手術中死亡,手術就到這裡終止,可以嗎?男聲幽幽開口。
於是哥哥再度被推回加護病房裡。意識提早離去,留下身軀,無助而被動地等著血液緩緩流乾。苟留殘息的時間長短,無人能預料。
*
「他就是從小太挑食,所以才會身體這麼不好。」外婆嘆了口氣,我只覺聽來刺耳,拒絕探究語氣帶有多少成分的悵然。
清新舒爽的三月,狹小的加護病房家屬休息室裡卻格外悶熱。驚蟄攜來的濕熱暖意正悄悄醞釀,生機在遠處無聲萌發。哥哥躺過的那個手術台,每天依然若無其事地迎接新生命在此墜地。
我將休息室有些生鏽的窗打開,涼風吹散房內令人不快的氣氛,卻無法替我帶走聞訊而來的親屬。我回頭看著有些疲於應付的母親,惋惜的話語像是關心,卻也拐彎抹角地評價母親的失職──「怎麼會有母親把兒子養得如此不健康?」、「怎麼會不糾正孩子的偏食?」隻字片語如同霜雪飛灑,一球一球的砸落在早已破碎的心上,水色的血流淌。
兄和我從小便耳濡目染西洋的文化,飲食大抵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後遺症──義大利麵、披薩與炸雞皆來者不拒,雖也不至於上癮,但不好中華傳統烹調的習慣卻在此生根。
雖然求學階段我便能逐漸適應吃便當團膳的生活,亦能成功融入親戚的餐桌社交,哥哥卻依舊對一桌臺式合菜興致缺缺,開始經常在聚餐時缺席,在遠離歡聲笑語的另一端,獨自低頭食用微波義大利麵或披薩。
「你兒子一直吃得不太正常,便是不健康的理由啊。」旁人理所當然如此在背後埋怨,替躺在床上、失去意識、插著呼吸器的現況,找到相當合理的前兆。
只是我和媽媽不制止而已──我摸透了他們話中尖銳的隱喻,畢竟無法解釋的噩耗,肯定也有注定發生的理由。
*
哥哥昏迷的前一天,我回家時已接近午夜,打開冰箱便看見他冰起來的披薩。晚餐食慾不好,他說,但現在想吃東西了。
我替他將披薩放進烤箱裡加熱,蒸氣讓餅皮上的餡料與起司更加軟糯,蒸騰的飄香從烤箱的縫隙中溢出,我轉頭問哥哥能不能分我一塊,他很快答應了。
我和哥哥的關係在重考後生疏不少,許多時候他興沖沖地從房門探頭,問我要不要一起打遊戲,卻被我以讀書為由拒絕。
「也要適時放鬆才會表現好啊。」他在門口滴咕,決心考上醫學系的念頭佔據思緒,我當然沒心情聽進去。
久違坐在餐桌前的兄妹顯然有些相對無語,我尷尬地低頭、鼓起來的金黃餡料佔滿視線,我快速將披薩塞進嘴裡,以回頭繼續沉浸在舒適的書海。他一直以來都不甚喜歡披薩的餅皮,默默將餅皮塞進我的盤中,而我正好喜歡香脆的口感,便乖順地將它啃完。
一切如同多年以來那樣,我沒有察覺任何異狀。
*
「只可惜太晚就診了。」醫師走出手術室時無奈搖頭。
他的晚,是指至少三年。哥哥的腦是偷工減料的房,外表看似正常,實則塞滿錯綜繁亂的管線,動靜脈之間缺乏微血管轉流,導致薄嫩細軟的血管壁承受比中老年腦中風患者高七、八十倍的壓力。爆掉是遲早的事,醫師言下之意如此。
前因後果似乎有了跡象。媽媽痛哭,爸爸怪她懷孕期間吃了太多葉酸,她怪自己沒能生給哥哥一個健康的身體,只有我尚找不到足以說服自己的緣由。
哥哥過世的前幾年,開始反覆的頭痛、發燒、神經痛,胃口也變得很小。他過去喜愛的食物已不再受青睞,轉而以蛋白粉代替正餐、經常吃清淡的湯麵省下家裡的開銷。頭痛劇烈時,偶爾選擇依賴布洛芬,強迫將自己推入夢鄉,以安定發燒的不適感。
與普遍的身體不適症狀相同,只是有點食慾不振、頭痛就吃成藥,沒什麼大不了。沒有人知道一些平凡的日常的小小病痛,背後交織著嚴重到足以讓人立刻倒下的病災。
沒有人知道,若至少三年前發現,壞掉的管線就有機會被修補。
*
手術結束後幾天,由於消化功能停滯,便拔掉鼻胃管,停止對哥哥灌食,改以注射葡萄糖液維持血糖。此時的他瘦骨嶙峋,病服上遮蔽身軀的地方像沒氣一樣消了下去,餘留肋骨凸起處如屹立的崖。我想掀開看看那塊布底下的模樣,最後卻不敢動手。
我捨不得看。看他被迫放下了生命裡的一切,此時卻在慢慢等待腦內的出血散開,直到鮮紅的浪淹及他的腦幹、生命跡象被舉數侵佔為止。
某天晝夜交會之際,終於迎來最後一次潮湧。
護理師拔掉生理監測儀的插頭時,儀器旋即回復到原始設定,生命與諸多數值一起從螢幕上消失。她拉起布簾替哥哥退下纏縛的病衣,體內冒出的管線也全縮了回去。在失去血液供應後,皮膚會迅速變得蠟灰,四肢末端浮起絳赭的斑塊。我握住他的手,發現有了溫度、屍斑似乎能再消退一些。他的五官輪廓如從皮囊裡注入水泥,永遠凝固在那裡。
當我想再回應曾經逃避的目光,遲來地抬頭,對上的只有早已闔掩的雙眸。
*
上天唯一留下的饋贈,是讓我最後來到一年四季日光普照的南臺灣。天光漸亮、城市甦醒,過度熾烈的炎日足以灼傷,卻也不疾不徐地替人蓋上金黃溫暖的被蓆、曬褪多愁善感與不可告人的傷痛。我漸漸學著在港都築巢。
大學室友告訴我人逢九必凶,然而我已不再信那一套了。由星象玄學宗教構成的人生預言與世間因果,依舊無法註解跌宕,說明為何家人離世與考上大學皆在十九歲時發生。大好與大壞、繁華與凋零、重生與殞命,命運流轉是轉瞬之間的一連串偶然,無人得以揣度、也無需捕捉它的行跡。
即使未來依舊瞬息萬變得令人發慌,至少時光最後的溫柔,是將沉積的回憶沖散得細碎,讓深烙的苦楚癒合成傷痕,將惆悵稀釋在歲月裡,直到散亂的、失序的生活碎片,再次被拾起。
於是我好像能夠走出來了,沒有預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