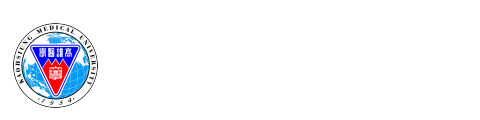小鎮故事
已經要兩個禮拜了。
聽聞附近又有人死去——就像剉刀劃下一筆,那木材微弱而絕對的力道反擊著刀鋒,即使看來鋒利如昔——但成熟的匠人已開始倒數了。
「政府幾天後就會攜帶物資與醫材抵達了!」山坳間的鎮長早就逃離這瘴癘之地,自瘟疫爆發後便是由一群堅信政府決策的志工負責鎮上的行政,或是催眠。
匠人的木雕工藝傳自他父親,父親的手藝則傳自祖父。在年幼時曾無意間找到族譜,翻看幾頁後便理解自己也將成為那個模樣,「但美不是一種模樣,」他父親遞給他傳家的刀具時說道,「而是生命在泥塵中混亂掙扎而起的複雜意象。沒有侷限與框架,也不會形成壓迫。」十幾歲的年紀,似懂非懂,然今日好像能從這十幾天以來體會一些。
他走出店鋪,避開為了糧食而大打出手的鄰人,走入山中。
政府下令封鎖小鎮唯二的聯外道路時,匠人剛從山上扛了一段雲杉木下來。他知道山的後方有其他聚落,但沒有路可以前往,而且要翻過這座高山並不容易;還有那群信仰堅定的志工,要是被他們發現試著離開小鎮就糟了。
「嗨。」匠人低頭劈開草木,應了一聲,「嗯。」大概三天前,住在菸酒行旁的寡婦跟上了這個小徑。匠人想知道她從何時注意到的,但他沒問。寡婦原本有一個兒子,「他死了,封鎖道路後沒多久就死了。」第一次照面時,話語逃竄似的奔出她的口中,匠人只是聽著,「我原本在菸酒行幫忙記帳,但他死後,我的字跡不再相同,從美麗得體變得多麼潦草倉促。他不僅將我的思緒、我的感官一併帶進了地府,就連圓潤工整的字跡也沒放過。」或許如果手指並無沾滿泥沙,匠人會試著伸手抹去滑過她臉龐的悲傷。「我們翻山,就走你開出來的路,直到盡頭。我們會往上爬,登上杳無人跡的亂坡。在這高山之巔上,高高在上的寧靜,靜到我能聽見他的呼喚。」
他們在清晨入山,以晨霧為偽裝,循著山的面孔向上爬,並在夜色的保護下出山。但路的盡頭很快就到了。匠人的傳家刀具並不適合拿來開山路,即使寡婦替他磨刀及搜集餐食——鎮上的糧食在政府補給的無限延期後,逼近瘋狂的稀缺——志工成為暴徒,當信任的根紮的太深,便將理智糾結、擠壓,最後粉碎。末日與滅村的預言被四處放送,同時充斥咒罵著山後另一頭冷血政府的穢言。「所謂信念不過是人們從整個世界當中選擇的局部,退一百步說,生活的本質就是找到適合自己的謊言。」在一片蔓草叢生之地,匠人細語,寡婦則回以一個融合了悲傷、藐視和欣慰的微笑。「但那每一個日子,那些談天,那所有的一切,都將凝聚成最簡單、最根本的事實,無法撼動,並永遠在我們頸後呼吸。」終於,匠人的刀具磨損殆盡,再也無法製作木雕或開路;他們的糧食耗竭,不足兩日。
「大概就是明天了。」滿月從黃昏的蛹中破出,掀起了夜的一角。乳濛濛的月光在樹林間穿插舞動,站在盡頭匠人望向遠方——幽深但依稀有光,如此零碎、透明——比絲絹要靈活、要羽絨更有份量,在林葉之上躍升而後旋落。是無邊無際的黑暗與光,巧妙自在的嵌入彼此,沒有爭奪且毫不擁擠,融合在最適合的位置,最恰當的依存。
「是的。噢,今晚月光真美。」微風吹嫋了寡婦的霜臉。這裡是盡頭也或許不是。
隔日,匠人與寡婦穿過嘈雜瘋狂的鎮上,像出門郊遊的孩子並肩進入山中,他們不斷地走,一面爬,一面哼歌,落葉斷枝在腳下窸窣作響。頭邊一聲輕嘆,輕微得只像被遏抑的情感在偷偷喘息。他們越爬越高,在繁枝茂林裡穿行,枝條在他們身上留下擦痕,泥水一再浸濕粘膩的腳踝。當那冷冽山風鞭韃頰側,鼓脹的耳膜隆隆作響之時,他們已越過了盡頭。
而山頂就在那裡。在自在舒展的鉛空之下。
雪白的山頭亮晃晃的,陽光灑落,暖暖的烘著兩尊冰冷僵硬的身子,天退得很高很遠,彷彿無著無落亦無憂無喜;而那組傳家刀具在雪地的折光裡,好似嶄新的一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