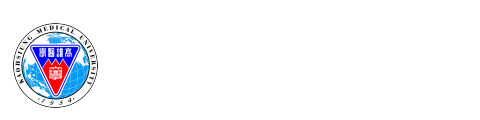車子駛過蜿蜒的山路,不知經過多少道小橋,穿過不知名隧道的另一邊,是山上的部落。初春時遍野的李花,是春天的第一場雪,將山谷點綴的潔白無瑕。此刻溪水已不再乾涸,在河床的群岩間緩緩流淌著,流向隱於深林間的瀑布,激濺起的水花往天空奮力躍起,似乎要將過去幾年間因疫情而遭受的桎梏、那些籠罩著陰霾的日子,通通一掃而空。我在多年以前看過電影「練習曲」,早該知道我們身處的島嶼中,有許多神祕美麗的角落,卻不知道所有美麗都該用自己的眼睛見證,那是超廣角鏡頭也無法呈現的驚豔與衝擊。
八八風災時被淹沒的村落,此刻已遷到更高處築居。當我們到達時,陽光斜映在遠方的山頭,在微風替山披上雲嵐後,更增添了一絲莊嚴神祕,山與藍天的盡頭似乎是另一個神的國度。教會的四周,屋舍比鄰而立,幾隻小狗慵懶地或坐或臥,沐浴在春天的陽光下,此刻的部落是如此靜謐安祥,彷彿那些創痛從未發生過。
當我漫步在路上,看見人們騎著車、大聲問好。他們告訴我,遠方的山頭,是當地人的聖山,我看著山巒連綿不斷,似乎沿著山走就能到達天界,而在那不可考的遙遠過去,人們又是為何逃離天空,走入了這幽靜的谷地呢?
人們也許會矛盾質疑,明明是一個如此靠近天空的所在,為何卻又離我們平時身處的世界如此遙遠?來時翻山越嶺的崎嶇,是部落人們下山求醫須越過的關隘,如此地遠,如此地長,如此地窒礙難行;在面臨生命危急時,彷彿要等待巨木化作彩玉般漫長而難熬,不知奪走多少求醫者的性命。部落中雖有診所,卻不若城市中有先進的設備,而眼科的資源尤為稀缺。當遇到白內障需要開刀、眼睛不適需要檢查,甚至連老花眼要配眼鏡時,多數的人選擇隱忍,就像當初面對日本政府「集團移住」的政策下也是選擇了退讓。
山上的夜,安靜地像使用了最新晶片的降噪耳機,一片寂靜中只見高掛的明月與滿天的星辰。在族人的傳說中,遠古有兩個太陽,隨其而來的永晝與熾熱讓人們苦不堪言,終於在眾人的祈求下,勇士拿起了弓箭射傷其中一個太陽,伴隨著日夜遞嬗,被射傷的太陽終成了月亮,溫柔地在夜裡照亮人們的路。在那些沒得選擇的時代裡,人透過傷害另一個「他」才得以生存;那在自詡文明、有無數選項的現今,是否就已經用不著刀槍了呢?而面對傷害卻能愈發溫柔的月亮,是不是才是具備現代人最缺乏的勇氣?就算是痛到在地上灑滿晶瑩的淚,月亮仍不忘關懷地上的人,多麼地溫柔,多麼地慈悲。
或許是受月光的溫柔感召,當天光逐走繁星,只剩來不及迴避的殘月就此昭示著我們義診的開始。義診時,我遇到許多長者,遭受飛蚊症所苦,有些有嚴重的黃斑部病變,他們看到的世界是怎麼樣的呢?藍天中會有黑影在竄動嗎?我小心翼翼地詢問,深怕會勾起他們心中的不悅。只是我在對話間卻感受不到他們的憤懣不滿,那是少數被遺忘在山下的東西。即便忍著眼睛不適,他們仍每日熱情地忙碌著,愉悅地與遇見的人打招呼。帶病的眼睛,似乎內藏著強大而閃動的靈魂,比起城中麻痺的人們更加熠熠有神。
一位伯伯數年前除草時被劃傷了眼睛,傷後留下的後遺症,讓他的視力不再像以往一般清晰。「這樣以後就不怕被老婆罵,說在路上偷看年輕妹妹啦!」面對我擔心的面容,他笑著說。笑或許在某方面是最棒的治療,我想到城市裡失眠的人們把stilnox劑量愈加愈重,夜晚面對空蕩蕩的天花板,卻仍舊趕不走心頭的愁苦。
在部落裡我與長者長談,與小孩遊戲,體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。山上的風很涼很清新,心中是未曾有過的溫暖。老人問我,城裡的人住在水泥裡,身邊的人都不認識,戴著厚重的眼鏡,成天想要拚第一,這樣就是快樂嗎?我只能苦笑,拿掉了眼鏡,我什麼都看不清楚,老人們卻清楚看到過去、現在,還有身邊的人。
部落裡的孩子,尤為親切熱情,對著素昧平生的我敞開心胸,把我當成真正的朋友;在城裡,人們卻彼此抱持防備,把遇見的人當作過客,只在社交平台上經營著平面呆板的形象,訴說著自己有多麼熱愛生活,卻未曾真正體驗生命賦予的深刻交流機會,我不禁汗顏。
多年以後,當我在職場中奔波時,可能會想起那個春天的午後,在操場草皮上與孩子們奔跑笑鬧,一雙雙細瘦的腿,卻是如此結實有力,往往讓我追逐到汗流浹背,卻又笑得開懷不已,那是真誠的靈魂與雀躍的心。
孩子們的擁抱,太過真摯,以至於我那在城裡打磨太久,冰冷的胸膛,竟有些承受不住。數日下來,我的胸中是前所未有的充實,臉上也不再有笑容以外的表情。孩子們總是大聲說著謝謝,我卻覺得自己才是最該說感謝的,是他們的笑容治癒了我冰冷狹隘的靈魂,讓我那如灰燼般黯淡的生命得以再次放光,我獲得的遠超過我所給予的。
無法忘懷的還有週末早晨,教會裡長老教我們的合唱曲。「Paiska Laupaku……」當歌聲響起,我看見遠方的陽光將山峰映的閃亮,似乎有什麼在緩緩呼吸律動著;「Mamananu……Oh he he……」眾人的歌聲順著河流,緩緩流向遠方。遠古的生命記憶,也是透過歌謠這樣代代傳承下來的嗎?即使遇到環境的巨變,生命依舊頑強、奮力的堅持;即便沒有文字,他們在烈日下流汗的身影卻憑著老人的歌聲,在族人的記憶中繼續行走著。
部落如今也不乏手機、電子產品,當然比起族語,年輕孩子們更常掛在嘴邊的是網路上的流行用語;部落終究悄悄改變著,與山下如此的相似,卻又如此的不相像,至少那份真誠樸實至今仍未消失,我暗自希望這份純粹能伴隨山間的風,吹拂到畫有百步蛇菱紋道路的盡頭,在月亮與太陽的照耀下永不消失。
臨別時,孩子給了我大大的擁抱,問我為什麼要到山下,要在那邊待多久,
我慚愧地搖搖頭,告訴他們要在山下待很久很久。山下的街道上,一條街開滿數十家診所,不到一小時的車程就能使用醫學中心裡的精密儀器,而城裡的人卻成天哀嘆的生活的不如意,看著琳琅滿目的櫥窗述說著自己的不滿足,這巨大的鴻溝是一兩次義診就能夠填補的嗎?我暗自祈禱著勇士能再次拿起弓箭,將那城與鄉之間厚重堅硬的牆給射穿。
孩子鍥而不捨的追問著:「還會再到山上來嗎」,我點點頭。
給不起任何承諾的我,心底卻堅信那會是在不久的將來。Uninang mihumisang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