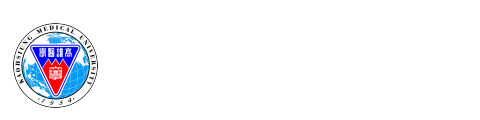女人跳下去之前,一個惡魔慌張的趕來。
「你等等,我這有個優惠方案,」他的犄角在頂樓陽光的照耀下類似塑膠的質感,「因為你現在下去會直接到我們部門,我加班好多天了,也想休息,」看著女人收回踏出的一步,惡魔欣慰地說,「接下來三天,你若不說超過三個謊,就直接把你轉到天堂去好嗎?」
那天晚上,準時下班的惡魔終於陪妻兒吃了頓晚餐;女人打開桌燈,想像著畫面。
隔天女人照例七點晨會,八點查房,十點門診。午餐時,一對夫婦來詢問女兒的病況。那個女孩早就不行了。女人看著排骨便當,虎口緩緩翻滾著竹筷,還好口中有食物可以咀嚼。也許護理長會在媽媽的第一滴淚擊落桌面之前來關心。
事與願違,女人還是吞下那口飯,她試著不要太冰冷,「抱歉,我在休息。」給出這種回覆,護理長和上帝也有責任吧。
那妻子有些嚇著,往身旁丈夫依偎過去。
女人看著男子攙扶著她起坐,淚眼婆娑還不斷欠身說不好意思打擾了。不自覺地,她低聲說道,「噢,閨女會好起來的。」
啊。惡魔深吸一口氣,又長長吁出,回頭繼續埋首工作。
第二天女人沒排班,過去這是她完整擁有的一段時間,會去爬山或看個電影,時間總是一下就過了。也許擁有本身近似於失去。
夕陽落下前,她鼓起勇氣打了電話,第一通接起來的是自己的母親。
那頭的聲音熟悉到不必見面也能想像細微的表情變化。女人亦明白,這不是不回家的理由。她只是有點厭倦設計好的選擇,包括非天然的興趣,符合期待的工作,此刻的生活。離家後,媽媽的聲音常有些顫抖,興奮和憂心的比例調得很謹慎。
不意外地,又是那句。「最近都還好吧?」
女人浸淌在橘光中,看著窗外。原來落日不是固態。她張了張口,閉上眼把落日擠下。
「......我好累。」
突然電話那頭如被驚動的小鳥,來回振翅希望找到問題的出口。女人只能循著慌亂的軌跡梳理那些對話。情感的獵網真是太密太細了。
「沒關係,不用急著來我這。嗯,媽也要照顧好自己,先這樣。」
結束通話後,女人訂了外送小火鍋,對著無光的天空食畢,打了下一通電話。
是另一個女人,她們認識許多年了。
接通後她脫口而出,「抱歉那天我認錯人了,不用想太多。」剩下的對話女人也不記得了,都是硬湊的。她坐在沙發上,腦中不斷回放當她趁著醉意親下去後對方如何驚恐地推開自己。
沒多久,女人笑著對話筒說晚安,抬眼惡魔正氣呼呼地看著她。「剩一天妳少說兩句好嗎。」
她用同樣的微笑說了晚安,側過臉睡著了。
午夜剛至,女人朦朧地醒來。她起身喝水,拿起手機百無聊賴地點開一個愛心圖標的app,猶豫一下,敲了最常約的她。
像回到家般,那人速速趕來後脫光走進浴廁,濕漉漉地換上毫無遮羞功能的睡衣,走近女人面前,「想我了?」隨後雙臂圍上女人肩頸,乳首透著睡衣磨蹭著她,軟糯的嘴唇在得到回答前便湊上去。
女人閃避了吻。她貼附睡衣女人的耳側輕聲說,「今晚認真一點,加五千?」
第三天的早晨,女人起得晚,她在亮晃晃的日光裡曬得有些暈眩。
睡衣女人已不知去向。
五千果然不夠。女人嘲笑自己的小氣,伸手發現常戴的那塊錶不見了。
她撥了通電話給睡衣女人,對方沒有接聽。她想告訴她那錶只是前年去日本旅行團送的紀念品。但第二通依然沒接。
第三通前,女人想了一下,傳訊息說門口有監視器。令女人意外地,對方立刻回撥了,「姊我不能陪你了,男友好生氣……可是姊我真的需要錢,我還有一個弟弟讀國中,」上次是說妹妹,但女人沒回話,「姊對不起,可以不要報警嗎?」
「姊溫柔又大方,遇見姊真的好幸運,但我也有苦衷,姊姊?你在生氣嗎?」
女人愣神看向窗外。耳邊嬌嗔的聲音跟她一點都不像,她們只有笑起來的單邊酒窩像而已。嘴唇也不像。
「我真的很喜歡姊,姊你還在嗎?」
女人噗哧一笑,「噢,抱歉,」她緩緩說道,「知道嗎,我也真的愛你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