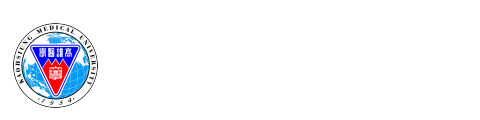朋友把傳單像回收物一樣塞進他胳臂時說了一長串廢話──「保證過。十四週。一萬二。」喬大抵用這三個單詞摘要。
手頭緊、高度近視、捷運通勤經歷滿三年,除了腳痠和無解的博愛座難題之外,總體權衡,喬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值得汽車駕照的人。
但他的朋友,這個剛剛才把團報優惠說得天花亂墜的人,眼看喬的臉色就要皺成他懷裡揣著的傳單,而拒絕的藝術即將體現於己身時,便脫口:「不喜歡。十天內。退全額。」──喬實在偏袒這樣不用重新消化的句子,像是喜歡一朵空有花語的蓓蕾,美麗而絕對。
喬傾心於這些附加意識的美好,而沒注意身旁的朋友早已悄悄地把表格填妥,並以享有早鳥優惠的勝利姿態,越身離去。
若喬此刻回神,他將會看見一片皺得像九月一般的灰色天空。他勢必會揣度著熨開它的方法,彷彿要整平一個季節似的,喬會十分專注,暗忖天空的秘密。
開課第一天,喬獨自前往櫃檯報到。選車、劃記時段、領取上課證,喬機械式地完成櫃檯小姐的指示,嘗試不讓複雜的規則和手續,提前滲入他為期十四週的考照生活──「因為精神,將決定預兆」。這是喬某天在電視廣告裡聽見的slogan,他始終弄不懂這句話的道理,但絕佳的記憶力卻顯得他如此深信不疑。
程序辦妥後,喬辨清車號,開門,調整椅背後坐定,旋即感到一陣睏意襲來,他承認自己昨晚確實被某些事情困擾──因這間駕訓班在網路上的惡名昭彰而失眠:駕訓班教練總是過分貼身、刻意忽視距離的拿捏。
多個不推薦的姓名、指控交疊於瀏覽和犯罪之間,喬謹慎地挑擇了一個從未見聞的名字,不存在褒貶的紀錄,單憑直覺。理應因一無所知而害怕的選擇,卻使得喬異常的平靜和安心。
副駕的車門應聲開啟,一個四十歲、體型曾經精實、會抽熱煙的男人,就以這樣簡單的句式浮現於喬的腦海。他用跌坐的姿勢上位,造成車廂微小的彈動。
「你開過車嗎?」喬用一個比車體搖晃更崎嶇的嗓音回答教練我沒有、我沒有開過。「你可以叫我南陽。」男人把口罩脫掉,臉頰上浮現一條像紋身似的淺疤,喬旋即投射一個害羞的意象,卻不欣賞自己這樣去耽溺。「對向酒駕、肇逃、終身不得考領。」男人指著疤解釋道,「這題筆試會考。」
接下來幾週,喬是如此在意著一條疤,彷彿是秋天的懲罰;隨風漸大,無人的車體竟也開始小小的搖晃。
最後一次上課,男人並未專注於喬的駕駛。他偶爾下車抽煙,偶爾靜靜地在燠熱的車廂裡出神。
喬害怕考照的時候,因沒有保持好距離而觸動管線,使響鈴大作;喬也害怕從後視鏡窺見一雙相連的眼神,像作弊一般,他害怕自己的身體出錯。
喬很緊張,雖然南陽叫他不要。他感覺車廂正在快速的縮小,必然的碰觸和擠壓已然難以克制。彷彿失靈一般,方向盤只能操控著喬不斷往下旋墜;柏油的場道佈滿警示,卻無視夜晚於其上奔走──喬無法反抗,只能任憑身體上傾與緩馳,像獲得一個全新的預兆似的──他看見一瞬間,南陽是青春的形狀。
「很好,你做得很好。」喬看見一月的天空被熨整的毫無隱私,如此誠實。
像是節目進入廣告一般,喬感受到意識的閃頻。他服膺於這樣曖昧、紮實的駕訓日,他嘗試釐清成簡短的詞句;但腦海裡,卻只能浮現幾艘鬆錨的船隻,隨波光晃動,彷彿這是決定性的一天,水手將要啟航。
手中接過滿分的場考成績單,南陽向喬簡單的道別,喬則傳訊息知會朋友測驗通過的喜訊。經過櫃檯,喬看見新的學員排隊報到,他猜想著南陽會如何指導他們;南陽會不會再次以自己的姓名,守護另一個純潔而無知的人。
一切的起始全憑預兆,但完好的結局是精神的產物。喬深諳的起始是,在一字排開的名諱裡,他明白南陽是他絕對的靈感;而完好的收束是,在領到駕照的那天,喬坐在終於不再縮小的客車裡,感受酒精包裹下腹的熟熱,把油門踩實。
決定帶著終身的禁令和疤痕,喬答應自己,要著迷於未來所有令人害羞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