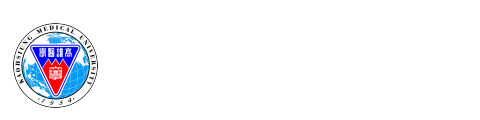一
睜開眼睛前,白耳畫眉的鳴叫聲順著風劃過林麓耳際。風穿過闊葉林的枝葉,向高處升高、滑落。風撞擊行道的碎石,吹動長尾栲的果實,鑽入林麓的髮梢,霧與沁出的汗融在一起。
他意識到自己身處山林,一座從未進入的山。他從不記憶山的名字,因為沒有什麼能完全表達一座山林純粹的本質與豐富的內涵。未被命名過的假山頭林麓認為也是屬於山峰的延續,於是他藉由植被辨認。偶遇的石瀑巨石,抑或幾株恰巧符合記憶缺口的植物,都是留下的線索。
二
獨自走往攀升的林徑裡,陌生環境時時刺激新鮮的真實感。他思忖著離島成長的自己為何如此迷戀高山,被海環抱的礁岸,怎麼養成不擅游水的四肢。林麓不討厭海,甚至稱得上喜歡。喜歡思緒被海浪打成細砂,飄向彼岸,卻不想裸身被水觸碰,他覺得赤裸的靈魂會被參透,會被發現是個冒牌者,不屬於這片海域。
「就像鯨魚的演化。」他思索著,從深海到陸地,再從河岸回歸汪洋。而他由海走入山。
五千萬年的演化也能發生在數十年的生命中嗎?無數選擇分岔成巨網,除了登頂的主幹道外,還有成千上萬生物的獸徑可以抵達,假若都能抵達目的,那麼生命是如何做決定的?或許是基因,但林麓更相信是自由意志的選擇,就像他選擇這座山。
三
「是你嗎?怎麼也在這裡?」
他們在這座山裡碰見,像兩頭野生動物在森林偶遇。林麓以為再也見不到他,因為他最終選擇走向大海。
「先不說我,十幾年沒見了吧。你呢?你從哪裡來的?」
「忘了,可能不重要吧。我已經走很久,還以為自己迷路了,不過遇見你代表路是對的吧。」就跟大學時一樣,我常走在你後頭,所以一下認出你了。
一同走在二葉松林道,山的呼吸與彼此的吐納產生共鳴。林麓想起那些日子,遭水鹿夜襲、肩並肩等待寒夜曙光的冰冷。日出照亮的那張臉,雙瞳是高山湖,鼻梁似山稜,而唇下的凹窩如圈谷般。
「如果一切重來,宇宙、地球環境依舊相同,所有物種乃至人類會走在同樣的演化上嗎?」
「可能吧。生物從分子的本質便想找到最適合生存的方式,也就是符合環境的最佳解。不同的物種都有其各自唯一解,就是對生態系所能提供的獨特價值。」
「能套用在同物種內嗎?倘若我是不擅飛行的熊鷹,渴望食肉的鳳蝶,」假如我就是叛逆的個體,林麓說,「能有什麼價值?」
「假設演化是讓我們在生態棲位促成物種獨特性,那麼同性戀、左撇子甚至遺傳疾病者的生命也有其地位,不是嗎?」
「那我們呢…我們之間的演化只能存在山裡嗎?」還是身體撤退都市,心靈奔向島嶼裡外。
「我不知道,但我能肯定當初我們都做了自己覺得最好的決定了。」
大部分時間是無話的,林麓卻希望這條山路能永不登頂。不要目的,只要能一直走下去。
四
「我們還會見面嗎?」
山頂的風橫行這片遼闊的箭竹海,呼嘯於群山與兩人之間,話只剩嘴型。
沒有聽到答覆,林麓卻鬆了口氣:
我們會忘記彼此的模樣回到都市,只有在山林相遇,才能以野生的面容互動。
「對了,你知道這座山叫什麼名字嗎?」
突然林麓迫切地想知道這座與男人相遇的山會有什麼名字。
「我無法知道,或許只有你自己知道他的名字。」
五
睜開眼睛前,風聲緩慢停止,歸於靜謐。
「林先生您好,您購買的三日深度睡眠防疫期已經結束。目前沒有感染的症狀,後續若有任何不適,請回醫院就診。」
林麓想起回國後,參加一套可以選擇情境的舒眠隔離。疫情在近十年不斷消長,病毒對人類進行天擇,如今發展出許多應對方案。
「醫生,我睡著的記憶來自現實嗎?」
「大部分現實會影響夢境,也有人認為現實是無數夢中潛意識的決定。儀器只是引導你進入相關的情境,夢境內容因人而異。如果沒其他問題就可以離開啦,您的妻子在外等候。」
床艙前的相片是一張廣闊山群,草原被晨曦曬成金黃色波浪,連接遠方的海平線。
林麓聽到了熟悉的風聲,像海濤,也像松濤,將山與海演化為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