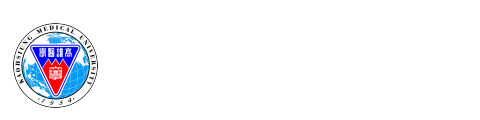有段話是這麼說:
「人的一生,要死去三次。
第一次,當你心跳停止,呼吸消逝,你在生物學上被宣告了死亡。
第二次,當你下葬,人們穿著黑衣出席你的葬禮。他們宣告,你在這個社會上不復存在。
第三次死亡,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,把你忘記。你就真正地死去,整個宇宙都不再和你有關。」
而曉琪認為,人的三次死去,一是對於童年逝去的死,二是社會性的死,三是當你認清自己的存在可有可無時,靈魂的死。而物理上的死,只是一個形式罷了。
六歲夏天,一個令人難以抹去記憶的下午,爸媽不在家,太陽暈暈澀澀的,光線穿透過落地窗打在地板上,曉琪還在跟妹妹搶玩具。電話響起時,是外婆接的,她叫她們在心裡跟佛祖求,可曉琪不知道要求什麼。外婆哭了,曉琪拉著外婆的衣角,將小小的手環繞住外婆的肚子,那天,媽媽沒有回來,爸爸也沒有。
隔天曉琪在夢中被搖醒,坐在眼前的是外婆和媽媽:「爸爸走了,不會回來的那種。」外婆表情凝重握住她的手,媽媽低下了頭,擤著鼻涕,手撐在床上卻不停的顫抖,曉琪聽不懂,說來好笑,前天早上爸媽出門都笑笑的說:我們下午就回來。
喪禮上,爸爸躺在那裡,閉著眼睛雙手放在腹上,曉琪問媽媽:可以牽爸爸的手嗎?媽媽說不行,這樣他走不了。可是她不想讓他走。
在那之後,外婆常在哭:老天你怎麼能那麼殘忍,他那麼年輕你要我女兒怎麼辦。媽媽總在為錢煩惱,在曉琪看不見的地方哭,常一句話也不說,抱她抱了很久。曉琪也想哭,也想爸爸,可她知道她一哭,她們就會更難過,所以她用指甲戳進手心的肉裡,當生理上的疼痛大於悲傷時,好像就不會難過了。
自此後曉琪很少表露那些情緒,她覺得那就是往別人頭上砸冰雹。難過委屈的事,像埋葬屍體般把醜陋情緒埋進土裡後在上方插上一朵向日葵,便可不再提起。
外婆喜歡在曉琪做錯事時開始啜泣
:「我曾答應過你爸,要把你們教好,是我命賤,是我沒用。」曉琪習慣將這些悲劇攬到自己身上,向外婆求饒。久而,外婆的話像條狗鍊,牢牢的拴住曉琪的脖子,無法呼吸。曉琪的童年是這樣度過的,上學,放學,吃外婆煮的飯,聽外婆的嘆息與責怪。媽媽在看不見的地方奔波。
在這些因著眼淚而淹沒的日子裡,她安安靜靜地溺斃了,沒有掙扎。
國中,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,對曉琪來說,什麼都是新的。在情竇初開的日子,曉琪也遇見了那個令她心動的男孩--她也曾認為那是她的一切。
國中的男孩抓不好與異性的分寸,不知道什麼能說,什麼話又只適合放在心裡和青澀的夢裡,那些騷擾的言論和仇恨的詞語像是縫紉用的細針,一針一針縫在曉琪的每一寸肌膚,一個拉扯都足以讓她撕裂。很多被曉琪視為夢魘的男生,夢魘總是在她背後說:「她要求太多了,明明沒有多好看。」、「我一定會讓她跟我上二壘。」一切的一切曉琪都聽在耳裡,也就算了,罷了。可說來諷刺,那個被曉琪視為珍寶的男孩在此時此刻沈默了,用這把沈默的刀,在曉琪的腹上狠狠地劃下一痕。所謂情感也只是膽小懦弱的謊。她決定向老師發出求救的訊號,可老師卻以一句:「他的成績那麼好,怎麼會做這種事情。」來打發她。
曉琪是被扎死的,被那些虛偽的一切、善變以及人性的醜陋。
在大學考試那年,所有的人都在鼓吹著同一種口號,讀好書,念好大學,人生才會理想。可曉琪上了大學才發現,不管怎麼努力,總有人能夠不費一毛就得到她汲汲營營想獲得的一切,不論曉琪存不存在,好像都無關重要,因為被看見的,永遠不是站在光環後的影子,擁有熱忱並不能說明什麼,所有想要的一切到頭來只是一場徒勞。
這一次的生命是她自己結束的,因為她知道她的存在不會讓人難過感傷,她定位不了自己,無法將真正的她栓在名為社會體制的建築上,所以她放棄了,墜落了,從高樓,她的靈魂。
自此,她只是形式上的活著,真正成為一個大人。